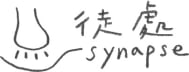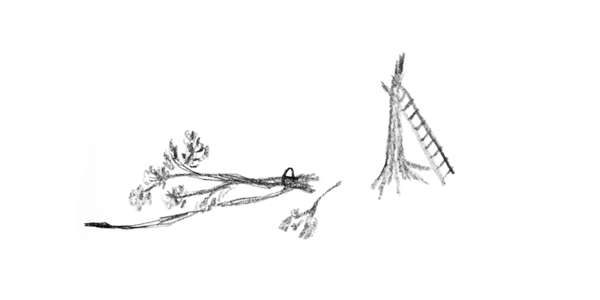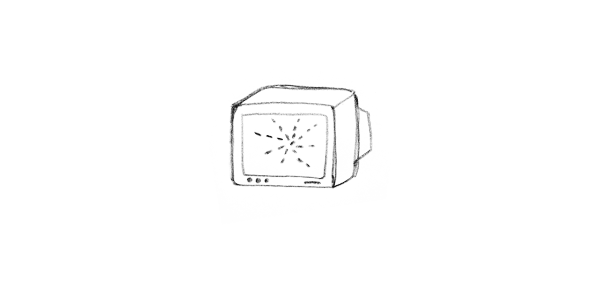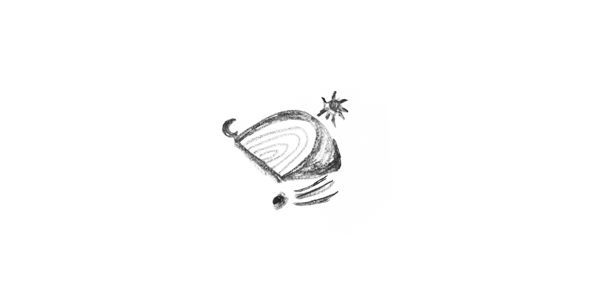±01 舊聞❞ 留家村:樹頂開花
樹是一段一段鋸下的,前面幾刀先要斜入斜出,製造切片蛋糕一樣的缺口。
「±」為首的標題是舊文,不過沒被讀過的舊文應當也算是新文。舊聞系列產出時間跨度不明,但總之都是以過去視角在過去寫過去發生的事。
〈樹頂開花〉寫於2021年8月,剛搬回南部不到半年,是為當時申請上書寫高雄文學創作獎助計畫所寫,為《留家村1》裡的其中一篇。最近城裡的黑板樹也開始開花了,夜裡或許你也曾聞到它的氣味。
還沒搬回高雄前在剝皮寮看了齣阮劇團全台語演出的小劇場,劇本是李屏瑤寫的〈家族排列2〉,劇裡有段描繪家族祖厝旁有棵榕樹,風水師說老樹已修煉成精,必須砍除,才能保家中男丁的壽命。演到這邊,想起黑板樹。
大概過往受實證科學訓練關係,談到風水總會第一反應覺得迷信,但仔細想想,老榕樹樹冠寬大、枝葉長得密實,雖能遮蔽日頭卻也影響採光,根系竄入屋子底下更難免破壞建築結構。前陣子回劉家村整理舊宅,猜想鳥兒不知打哪銜來榕樹的果實,種子落到窗台,樹苗沿牆面蔓長到二樓蓄水池,根撐破毛玻璃和木窗框。小樹的莖長成了水路,夏季雨水便如此積淹到一樓。
風水師說久無人居的宅邸易壞是因為「沒有人氣」,另一方面大概也緣於欠缺打理。又好比房子坐北朝南更好,是為能避掉嚴寒的北風;吉凶禍福,風水也不總是沒有道理。
現在的住家是我出生後才蓋的。因為土地橫作東西向,西側臨馬路,家門便開向東方,正對著三畝的廣場和苗圃。屋前植了四棵黑板樹,恰好能稍微遮擋太陽東昇斜照入室的光,後門則是一株福木和金露花,屋子繞著一圈矮仙丹。
那四棵黑板樹後來長得有五層樓高,相應地樹根也就扎得深,使鋪過水泥的廣場隆起多處能絆倒人的迷你山脈,甚至蔓進廚房地底,把屋內磁磚掀起一塊,雨天時候水就倒灌進來。忍了幾年,再不捨也不得不為房子打算,便將它們都砍除了。
爸媽經營園藝,栽的其實不過是掌心大小的觀葉植物,但所有院子裡的事他們都喜歡自己來。架上長梯,砍樹的技巧是,如果你要樹傾倒時不傷到房子,那就要綁上繩子往房子的對向拉,並且在那之前還得先修剪過枝條,使視野盡可能清晰,也減小落地後會波及的範圍。樹是一段一段鋸下的,前面幾刀先要斜入斜出,製造切片蛋糕一樣的缺口,一面下邊拉繩子的人有節奏地配合向外施力,最後才一鼓作氣截斷,讓整個樹冠隨綑綁的繩子像流星那樣被地球引力曳著拋丟下去。繩子只是定向用的,一旦失了基點,事物在墜落的時候並不需要拉扯。
〈家族排列〉裡所描繪的砍樹過程則是:「總之媽媽立刻找工人來砍樹,還找人來做法,因為聽說,老樹是不能亂砍的。」在心態上謹慎小心地對待,可那權衡與凝視的仍是身為人類存在之無端恐懼,「近百年的老樹,一個早上就砍掉了,叫了怪手,連樹根都刨起來⋯⋯」起心動念於愛,卻將細緻的儀式感揉入暴力,感覺更是可怕。
在樹還長得茂盛那些年,我們曾在樹間綁上吊床,午後防火巷的風輕盈地包裹住青春期的我,腹上蓋著課本,盪著盪著就睡著了。也曾有幾個太過炎熱的夏夜,我試著在吊床上睡了一晚,而初次感覺到置身於無邊際空曠戶外的那種恐怖。偶然睜開眼,從樹縫中瞧見星光,想起「樹冠避羞」,也像是水泥地因樹根撐破而產生的裂縫。天上地上兩相映照,夾於其中的我們遂又縮得更小。
由夏轉入冬,仰頭探的時候,氣味就降下來了。如同午後涼風包裹,晚上夜色籠罩。
黑板樹開一叢叢白綠色的小花,視覺上並不顯眼,可不能忽略的是氣味,尤其在入夜後更濃郁。對黑板樹開花氣味的敏感,最早其實不在家裡。大學住學校宿舍,在第一個離家的冬季,經常要偕不同寢室的朋友到吉林街上覓食。高醫醫院那側自由路上整條行道樹栽的也是黑板樹,最初還弄不清那辛嗆的氣味何來,待夜愈深,車少了,整條街上只剩寥寥行街的人,還有樹。被氣味牽著頭往上仰,才疊合起離家後的答案。
我還記得一個味道,是早期映像管電視被砸碎之後會散發的一股化學燃燒的氣味。有個晚上,他又帶著醉意前來拜訪。那陣子入夜後家裡經常只剩我和媽還有阿媽,剛上國中的姊姊則到臨鎮去補習。阿媽要媽待在浴室裡別出來,但喝醉的他其實不曾真正動手要傷我們。應該是那次,他說了一些話使我非常憐憫——我其實意外,在六歲那個年紀,我竟是在恐懼背面認識了無奈——他大抵是說:「有一工我佇灶跤對後壁攬阮某,彼時陣我著知影代誌無共款矣。」一時激動,他便將電視從電視櫃推到地上,匡噹,沉重的玻璃面板和其他零件結構碎噴了一地。地上都是他的血。那麼多次,我真的未被他傷過。
那晚的記憶我只到這裡了,他之後仍有再來,壞掉的電視則被堆在植黑板樹的花圃裡面好段時間。畢竟我生來還是個理工腦的孩子,經常去翻探它的結構——電視機玻璃屏幕之後原來是個黑洞,留著一個漏斗狀的空間,面板間還夾著一層薄薄的金屬膜,是要讓電子束投射到屏幕背後顯像。
林強一九九四年發行的《娛樂世界》裡有首〈盒子內的時間〉,整首歌詞很短,僅僅六句:
時間被關在流動的空氣中
風聲鑽過窗縫牽成一條圈圓的旋渦
冰冷畏寒無色彩的光束
盒子內縮成一團形體
在空中飄浮塵土的精華
光影不定慢速進行
盒子裡的空間之所以存在原來不為裝載物質,反而是必要一點距離才能撐出電子束於屏幕顯影的範圍。早已搬演完的劇情透過訊號投遞過來;都是演完了,才傳送過來的。那台電視被砸碎之後〈盒子內的時間〉沒有被釋放出來,倒是我的童年在此形成斷代。
後來好幾年家裡沒再添購電視,而隨時代進步,電視的形體從「盒子」成為一片「板子」,影像接收與傳遞的方式也不再相同。類比訊號在不受干擾下,更能反應原始,但還記得那些颱風夜嗎?接收訊號的天線卡在屋子和樹頂之間隨風晃蕩,想看停班課的資訊,還得忍受三層任立渝的臉疊在一塊兒跳 popping。數位編碼則是種全有全無,只會直接出現「no signal」斷訊畫面。
影像傳輸歷經類比到數位的過程,記憶也從身體感覺與畫面慢慢被我文字儲存雲端——然而氣味,無法被編碼成數位,只能透過四季流轉,體感溫度漸降、樹花逐開,使分子再次進入鼻腔,勾引記憶顯像於前。
在台北工作那幾年,公司位象山站,是信義區靠山邊藏著的一片豪宅裡的地下室。台北冬臨必定較高雄早,在白露之後就頗有南方冬季的味道;此時的陽光是液態的,會透過樹冠之間的隙縫滴漏下來,把整個夏季悶住的暑氣蒸散帶離地表。
先開花的是白千層,接著才是黑板樹,氣味都很濃郁,只是總被稠密的人車流動沖散未必能被發現。而真正入冬之後盆地總雨,把上下班的路徑打得很濕,撐著傘同時眼睛也緊跟著地,就怕踩到被樹根鬆動的連鎖磚噴濺出泥水。黑板樹的花亦被打落一地,和著雨水鋪成了黃褐色的毯,踩著踏著就黏鞋底帶進了辦公室。忙碌異常的四年,經常深夜十一點才打下班卡,無人的社區,只有這時候氣味才靜靜又降下來將我籠罩。
每年黑板樹開花的味道,都會把我的意識帶回那些片刻,像一口瑪德蓮就要普魯斯特替它寫下整整四頁。
在剝皮寮看戲的那天又是剛要入秋的九月,演出結束後我散步到附近龍山寺裡晃了一圈,恰遇上祭祀的日子,聽信眾跟著廟公誦經的聲音,眼睛閉著。那陣子Y的爸爸在加護病房裡待了有一個月之久,我心裡總惦記著他的難捱與疲憊,沒想到才回到家,室友用著探詢的口氣問我:「知道了嗎?他爸早上過世了。」聽說是在高醫走的。後來我和他說我看了那齣戲,只是沒說戲裡的爸爸最後也是死了,也沒說要不是他我或許也不會搬回南部。那樹砍或不砍掉似乎也無關於最終的運命嗎?城或鎮裡隨處可見的黑板樹,栽在人行道、分隔島或家門前最後被砍掉,總是要到夜很深很深的時候,花開的味道才會降到獨行的人身上。
重新返家,發現屋前的黑板樹砍去之後,根系竄起如板塊運動造過的山竟也隨之消去無蹤。凹凸不平的水泥地塌了回去,再也見不著樹冠的天空一片乾淨。
只是回想,當年擾動家的地基的,原來並不是那些看得見的東西。
如上信所說,當時剛離職搬回南部就遇上疫情三級警戒,手邊關乎家庭採訪的案子都暫時停擺,原本想去午營咖啡兼職打工的計畫也告吹。閒來無事,只得找點賺錢的方法,就剛好被書寫高雄徵獎計畫下到FB廣告。六月截止、八月公布名單,幸運以《留家村》為題獲選,是一年期的計畫,結案須交以五萬字以上文稿供審查。寫這批稿反思很多,關於記憶作為敘事、關於書寫作為治療,完成後蛻了層皮。再去重讀,偶有痛苦,但彷彿都相當遠了,倒是當時為每篇文配上的延伸歌單,點開還是覺得非常好聽。這一系列單篇讀來可能會有點隱晦難懂,文字也稍比平常繞嘴,但算是滿真誠地記錄下當時自己的狀態。
李屏瑤的〈家族排列〉原是2016年第19屆台北文學獎舞台劇本組的優等獎得獎作品,後有收錄在2022年《死亡是一個小會客室》劇本集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