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舊聞❞ 留家村:愛河岸邊沒有留言
我們以為此生是要在一條條平衡方程式裡求得最大靜摩擦力為正解,卻忘了落筆與發語,那一詞一義,以及前行或者遁走,拾貝與取火,都源自次次與異質觸碰的機緣以及必須,其中甚至無涉於接觸面積。
去看巨轟演出,聽魏talking聽到差點掉眼淚。2013年畢業後我就上台北念碩,與高雄的道別有點狼狽,無論和系上朋友、樂圍或家裡,都有些微妙而掐不清的思緒。即便我經常懷念,卻仍感覺上台北有些逃的意味。不過都是十多年的事了。2022年拿了Y的票去大港,睽違那麼久與猴子碰到面,是真正大學畢業後再也沒見的朋友,回家後和猴子聊天想起許多大學時愛河岸邊沒有留言的事,遂寫成了這篇。
這幾天把去年讀一半的《Stay True 保持真誠》帶在身邊,讀到後來也一直想起當時寫的這篇。曾經有那麼一群人,以極浪漫的方式影響著彼此的青春年少。分享書、電影和音樂,他們一夜至少花掉一杯酒錢,而我賺入三小時時薪。我們偶爾批判資本主義。
我到現在還是很執著於當時問猴子關於「快不快樂」的問題。巨轟演出結束後,我們窩在酒吧外繼續聊天不捨離去,我問猴子這一年快樂嗎?問魏這一年快樂嗎?猴子反問我:「快樂重要嗎?」魏則說他快樂。我聽到就好高興,對著猴子大聲說:「對吧!我就說我覺得他有比較快樂!」不過事後想想,對啊,為什麼我覺得快樂這麼重要呢?
不曉得,但我還是覺得,每次相聚的我們都比平常再快樂一點點就好。快樂就好。
——2022/6/18
Y為了考試不能去大港1,把票讓給我。前一晚先去了趟前鎮跟他朋友拿票,還在LINE上說著太魯閣大魯閣、鹹蛋飯糰還肉臊蛋餅之類的爛笑話。我實在太久沒去大港了,不管是早餐店還音樂祭,都是快十年前的事。隔天一早從大湖搭車到美術館轉輕軌,先停了站文武聖殿吃刈包加蛋,又點一瓶牛奶,老闆說裝袋子喔!就把高大牧場的牛奶從玻璃罐倒進塑膠袋,用同樣艷紅色的繫繩束起。
三月底,高雄已經熱到極致,換手環時我內心邊安排著想看的團序。上次來大港已是2013年,大義、蓬萊和棧貳庫都還沒有開放,現在突然場區打開這麼大2,光從海音館繞大港橋走到九號碼頭就要十多分鐘。跟赤炎的太陽和演出時間表斤斤計較著,疫情關係,也不能在場內喝酒,三十歲聽團竟要那麼清醒。第一天沒聽多少團,百合花之後淺堤未完,繞了大圈去休團未免也太久的閃閃閃閃,後青春的心情在〈一瞬之光〉唱到「你的笑浮現/我已經改變/Meet me at you 25」幾乎爆炸。還未酒,還能跳跳跳,結束後轉身就看到z推著嬰兒車站在劇烈音場範圍外護著小實的耳朵和睡眠。
當年跑音樂祭的人都一個個生小孩了,喔,還有那些台上的也是。我們到飲食區攤販買水果酒,拆開Y買套票含的毛巾,蓋在實的推車上。高雄很熱對吧?不久前我們才剛在新北的Zepp聽淺堤,晚上的表演,結束後就搭他們便車從新莊上高架複習高雄的音樂,慢慢地晃回新店。實才一歲半就懂聽團,我們接著去室內場避暑,有點chill的問題總部帶起嬰的grooving,她從身體到腦袋都那麼開心。
潘沿也是在Mage肚子裡就懂聽搖滾樂的小孩,認識她們的時候我才20歲。大三那年孝順街上開了家「Caf’e Bar The Way 」,中文就叫「樂圍」,青草綠的招牌在夜裡亮起特別顯眼。從高醫東側門走過去不過五分鐘,開沒多久學生們就聚過去,和當時交往的對象約好了要一起去光顧,但倒是分手後我才很突然地開始在那邊打工。Mage開店時就已經懷孕,但盤子的建築師事務所在台東,夫妻居隔二地,我常深夜一點多騎機車載Mage從三民區沿著同盟路帶她回鹽埕。潘沿一直都聽我們在店裡放的歌,有時候是熊寶貝,有時候是草莓救星,還有1976、929、Yuck之類。不過她最愛的是Rivertree。她總有Rivertree的現場可聽。
那幾年高雄看表演的場所除了月光劇場,還有水星酒館3和藍色狂想,取向是不太一樣。樂圍大概又是第四種,只有一個小小木頭站台和一把吉他,學校山杏社和幾個醫學系學長組的Rivertree成常客。
玩團、聽團的人在高雄念書,都特別嫉妒後來上了台北的同學。那幾年地下社會還在,大概以為成人後能親自見證,卻就成了絕響。The Wall還是河岸留言啊,那種彷彿要在雨下到必定使人憂鬱的城市才得成立;也不知道是不是勞比個性的關係,魏寫的詞再無力,他唱來卻總是很明亮。我每次聽〈愛河岸邊無留言〉「因為太陽太大/我們不太講悲傷」這句,都會忍不住笑出來。那幾年Rivertree經常到處表演,有場在台南Room 335唱〈歲月〉,樂迷放上網的影片裡,魏在演出前說:「我現在很苦惱,到底要不要當醫×呢?」這個苦惱跟了他很久。我畢業那年魏也大六即要離開校園去醫院實習,畢業典禮前幾個月,他們在月光劇場結束專場後大夥兒又聚回去樂圍,魏走到站台拿起吉他,說:「我今年24歲,我愛我身邊所有的人。」(那麼年輕的樣子,簡直令人不敢相信)接下來整間店都是〈歲月〉——
每天早上我都被迫要起床 騎著機車往同樣的目的地
省道左轉一直走就是墾丁 海浪一片片並不用力說服你
因為我還想表演
因為我花了好多錢
因為我想當搖滾明星
因為我不要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還抱怨
而到我24歲的時候,他還是當了醫生,我們都在早已沒了地社的台北日復一日。
大港第二天,z依然是帶著小實在城市裡四處避暑,還去了龜時間吃頓慢又好的午餐;我早上也沒趕著進場,倒是先去了三鳳宮拜拜,才沿路散步去聽最後幾首必順鄉村。在黃玠國時,一個已經喝ㄎㄧㄤ了的年輕女生突然拉起我的手,要我跟她一起跳;她身旁的朋友急忙要替我解危,我覺得好笑,和她閒扯,頭卻反被她巴了好大一下。想到Y說有年嘉義的覺醒音樂祭還有人喝醉在泥巴裡打架,被巴這一下倒也還好,大笑著跟她們說等等傷心欲絕見吧。沒多久,猴子傳來訊息,是張他畫大港的速寫。猴子就在港邊畫圖聽每個舞台的聲音在海面、船舶與棧庫間反彈,音場還出奇地好。我找到他,一齊坐到港堤後他便停下筆,自從我畢業後我們也已經九年沒見。
猴子最早是Rivertree的樂迷,後來變為朋友,也成了樂圍的客人。他那幾年都在寫影評,除此之外我對他毫無認識——年紀、職業、所學專業等等,一概不知。從他手上接過唐吉軻德封面筆記本,一頁頁聽他講4,如何又後設又蒙太奇地拼貼故事成畫面。他說了一堆人、專輯、電影,我都搖搖頭說沒聽過,只捕捉到 Pavement 的〈Here〉和 Joy Division 的〈Isolation〉說要回去聽。他和魏到現在還是那麼好,連漫才和科幻作家都能聊,遂畫下了一片花團錦簇裡,巨大章魚抓住《2001太空漫遊》裡頭太空艙的圖,然後再跟我說了《戀夏五百》裡頭披頭四〈Octopus’s Garden〉的故事。
我讀著他們的對話,只能嘟囔著拜託,你們談的太難,不寫影評了,那你寫畫吧!但因而聽得入神。兩個小時過去,高流那邊舞台,鄭宜農已經唱到剩最後兩首,我為了故事寧可沒趕上,卻也好在〈囡仔汗〉時恰恰與z和小實會合。那日的壓軸場是美秀集團,實已在嬰兒推車裡熟睡,D的拍攝也收工,我們雖然仍遠遠站在音場之外,但身體的快樂會甦醒,會感染。遠遠地,z和D繞著推車奔跑跳躍,像從未成為母親、父親那樣。
後來猴子整理了畫冊裡的歌單丟給我,還有魏宅錄的demo。我點開聽,開玩笑說一直在等鼓進來,「好想聽full set5!」他說:「結果這麼多年後,還是跟在樂圍的情境一樣耶。你在聽一個喝得半醉的人講話。」我看著笑出來,其實沒發現一點醉。茵茵以前會在樂圍待到睡著,我們就騰出側邊吧台的桌面,把她抱上去蓋條小被。咖啡機在晚上的作用只剩熱牛奶給小孩喝。想到魏有次喝醉,猴子騎著機車把他送回建工路上的家,而我就在後頭跟著車,看他倆的背影在深夜無車的大道上緩慢前行。一股溫馴的憂傷。這幾個月經常去高雄市區晃蕩,可畢業搬離城市後其實再也難再目睹那裡的凌晨與清晨。猴子前幾天說他沒想過魏快不快樂,我也在想為什麼我會覺得他不快樂?會不會其實那個經常不快樂的人是我呢?就像魏說猴子是他看過最不快樂的人,但猴子自己也不這麼覺得。
「在黑夜包圍裡惡夢醒過來/忙打電話給世界級的影評人 全被否決/你的內心 藏著許多 無法猜測 冬天的夢」,魏在〈College Version〉寫冬天的夢,我猜是費茲傑羅的《冬之夢》。那時候猴子拿了這本書來店裡借我,爾後還有一個隨身碟放著《花神咖啡館》整張電影原聲帶和《一一》無字幕全片。畢業後搬到台北,住處就在《一一》裡NJ一家住的羅曼羅蘭大廈後邊。某天我再想起《冬之夢》,在社群上放了〈College Version〉這首歌,卻收到N的訊息,有點央求地希望我將回憶的音量放小。我後來沒再找到這則訊息,總懷疑這是否僅只我的潛意識在文字對話框裡夢囈,如同我總是在現實的大廈玄關找電影裡的血印。他的聰明足夠在文字裡藏著頑皮的慧黠,但也因聰明而更常在其中發現生命的破綻;畢竟科學裡談的總是μ=0,才能得出理想於運算的重力加速度,可我們終是被空氣包覆,養成了適應21%氧濃度的身體——所有物質或意識,在碰觸時即因摩擦力產生能量的發生與散逸——而我們以為此生是要在一條條平衡方程式裡求得最大靜摩擦力為正解,卻忘了落筆與發語,那一詞一義,以及前行或者遁走,拾貝與取火,都源自次次與異質觸碰的機緣以及必須,其中甚至無涉於接觸面積。
我記得2013那年大港某日壓軸場是1976,舞台在靠11號碼頭那側,我和魏還有阿辛逆著霓虹閃光沿港走進人群,所有人的側臉都成了剪影。阿凱〈耳機裡的新浪潮〉才唱一段我就哭了。當時的上個年底阿嬤剛過世,接著我研究所推甄申請落榜,是不太容易的一年,覺得一切對文化能如何抗衡資本的想望都離我好遠。但現在再回頭看,卻也依然感覺幸福。
喬治・史坦納在《勘誤表》裡面一段講述音樂,「面對音樂時,語言的神奇同時也是它的挫折」,他引用維柯(Vico)、盧梭、叔本華所主張觀點,論音樂先於語言且又不隨宇宙終止而消逝的特點——「音樂代表存有(Sein)的最重要本質,是存有本身,它的活動形式比語言的形式更加直接自由。」那一個又一個偶然卻龐大的現場,用再多的字詞描述,都令我同他所論地感到挫折,不得不用上整個身體去記得,忘記,再記得。史坦納在末段寫說,「奧菲(Orpheus)因著理性的不耐,向比死亡更強的音樂回首之際,便退縮成詩人。」
上台北第一年的冬天還在羅斯福路上的Revolver Bar看過Rivertree和老貓偵探社的合演場,是最後的巡迴演唱。之後他們幾乎少再一起玩團,五個人都已成醫生,其中三個還當了爸爸。有次去台東找Mage,她說潘沿一歲多時會用糊糊又奶奶的聲音討〈Party〉這首歌做搖籃曲,明明是節奏那麼明快又吵的歌,唱說,「就像是就學貸款/和酒精在血液裡代謝我的壓力」,卻能使她安穩入睡。
我們不知不覺都活過了歌和書裡主角的年紀(也認真要把就學貸款還盡),卻仍總是能在場子裡巧遇誰,然後相偕著從一個又一個音符碎片中遷徙。在那個還能一手提酒,扯著喉嚨,卻仍得(也還能)看嘴形才能辨識話語的年代,「我曾經醒來/我曾經睡著/我曾經也做過許多夢」,摟著旁人肩膀、搖頭晃腦的歌唱成為一指播放鍵,理想在地下捷運車廂裡與日子競速,直到〈耳機裡的新浪潮〉繼續播到「嘻皮們都剪了頭髮」這句,遂才想起村上在《1Q84之後~》長訪談裡說的:
當時的我們認為那時的大人既愚蠢又貪婪,社會意識過低,什麼都不思考,才做了許多愚蠢的事情,不過等我們這些理想主義者,擁有先進意志的世代長大成人之後,世界一定會變好。現在想起來是相當脫離現實的事情,但當時的年輕人大概都相信這個。
說什麼「Don’t trust over thirty.」,即使被取笑說大家有一天不也都會變成三十歲代嗎?但還是確信我們將會變成完全不同的三十歲代。就算學生運動被壓制下來,還是相信我們成為上班族後,公司本身會改變,很多人把頭髮剪短進了公司。至少我周圍有不少這種人。但如果要問那麼社會因此而改變了嗎?答案卻是絲毫沒有改變。
開始接案工作後,偶我上台北開會,空檔時候就抱著平板去河岸留言樓上海邊的卡夫卡寫編稿子。經常遇到阿凱在那裡,或和人開會,或靜靜地做自己的事情6。記憶裡那些唱著「愛河岸邊沒有留言」的大男孩們不再上台了,然而我也變得不必仰望音樂,因為我就在音樂裡面。
村上活得並不像他自己說的那麼悲觀吧?依然是本能地抗衡著什麼,使我內心十分感謝曾經那些剪短了頭髮的三十歲代。而我也已經成為三十歲代了。
〈愛河岸邊沒有留言〉的書與歌單:
〈一瞬之光〉閃閃閃閃
〈耳機裡的新浪潮〉1976
〈歲月〉、〈Party〉Rivertree
《冬之夢》費茲傑羅,一人出版
《勘誤表》喬治・史坦納,行人
《1Q84之後~村上春樹長訪談》,時報文化
(2025/1/14後記)
寫這篇時真的沒想到,後來還能看到魏和喬辦的演出以及轟鳴重組,看到魏寫在轟鳴的貼文上說:「我總是在練團或表演喝太多的隔天灰頭土臉的進醫院繼續打報告,忍不住跟擦身而過的放射師說,你知道我最近在當明星嗎?」整個大笑出來。〈歲月〉裡寫的成真了!工作同時還是當了搖滾明星!天啊!
每次和他們聚在一起,我都有種不至於將青春扼殺殆盡的倖存感。或者透過對照而見證了自己順利地退行(regression)。
去年底去Zepp看大象體操,場內遇到好久不見的Su,我們一起回市區的機捷上聊天。我們第一次聊回過去,她說,她以前感覺我對店裡的人事物總是「冷眼旁觀」的樣子。這點,似乎和魏說的「微不足道」相當一致,所以也不大訝異了。只是我以前沒想過這會令人受傷。但其實我那時是,非常非常的羨慕他們,能有歌就唱、能無來由大聲地笑鬧,羨慕到感覺格格不入,也無奈於自己對展現情緒本能性的節制。但也慶幸有一條吧台,讓我以另種形式很好地和他們待在一起。我一直記得猴子以前說,他覺得我是一個即便看起來難過也不能被摸頭安慰的人,「感覺像褻瀆。」形容得真好,哈哈。
抱著這樣的疏離畢業、離開高雄,曾是我在台北生活那七、八年間的遺憾之一,而經常在台北數個深夜咖啡店裡想念起以前的生活,早秋、暗角、巴黎米、小地方,等等。殘留的影子,有些店也隨時間消逝。幸好,在我已經變得任性許多之後再和他們相遇,終於能很放心地對朋友們表達愛了。






上封信提到在大港橋邊和Y討道歉不是這次啦。哪有人拿了人家的票還罵人的。
嗯⋯⋯據說今年場區範圍更大,趕場可能要搭輕軌或騎ubike(?)昨日與朋搶票成功,我們大港見!
以前經營水星的老闆後來在高醫附近開了百樂門,不過百樂門開業時我們已經從大學畢業了。前年才為了The Tic Tac第一次去,想像學生時期若有家離學校這麼近的live house該多幸福。
猴子畫完一本就會把畫本送人,那天轟鳴完問他最近畫什麼,他拿出「椅子 izu」。然後我們窩坐在酒吧外頭的地上,他也畫下了那晚的椅子。這本明明還沒畫完的「椅子」暫時在我手上,接棒偷畫幾張。
去年如願,雖然不是full set,但聽到魏演出了這首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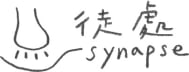





好好看喔
我也很羨慕你能長成仍保有當時熱情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