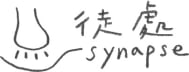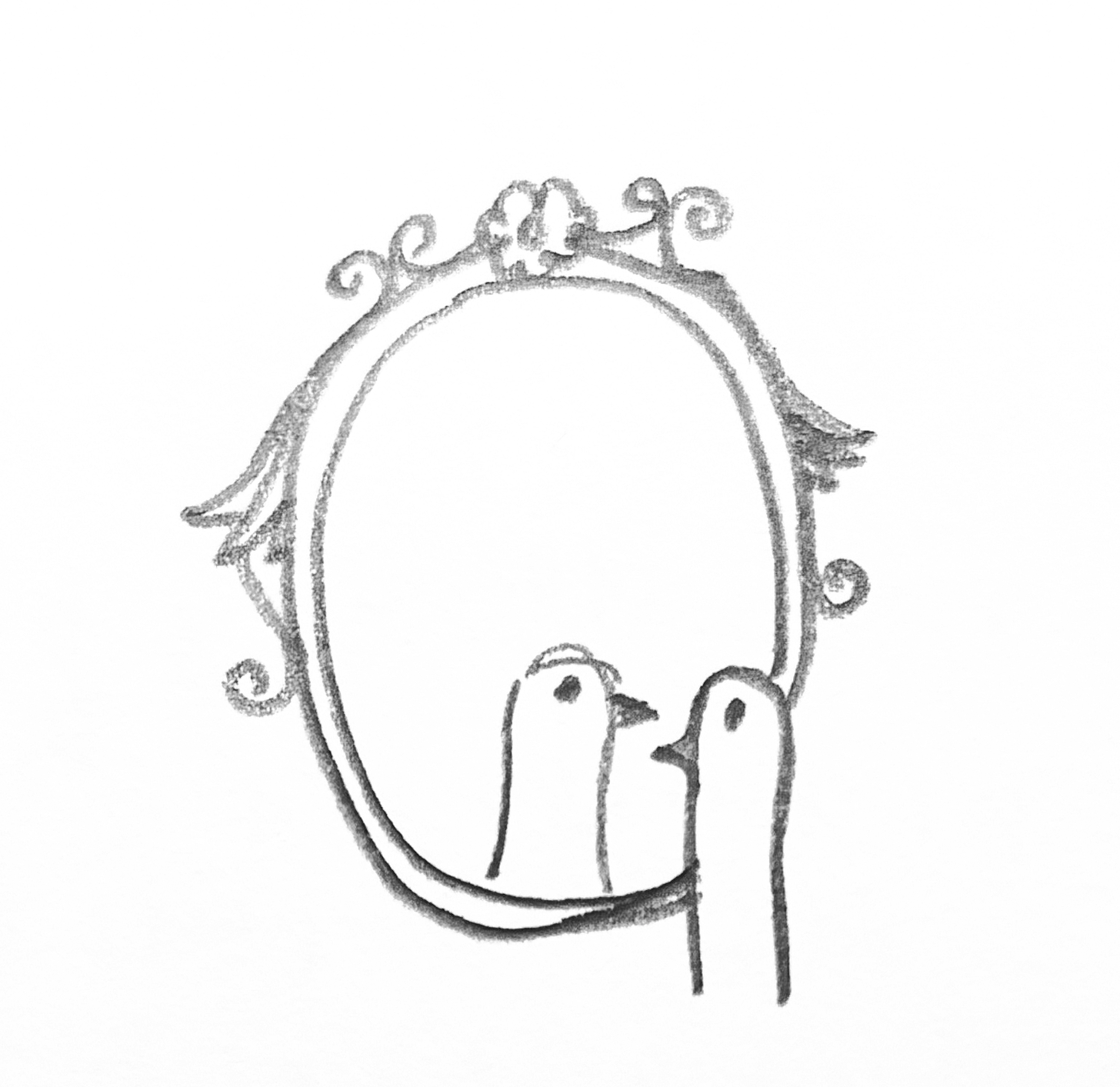±08 舊聞❞ 留家村:倘若鳥也有童話
我不確定自己是到多大年紀才意識到那樣「殘忍」,也或許由於我讀不懂豆娘與青蛙的表情和語言,好奇探索的本能先行,鏡像神經元置此無用——從而知曉人或許未必擁有同理與憐憫的本能。
——20220814
凌晨響雷落大雨,我聽得難受。
傍晚照常,工作後出門騎車,經過一片魚塭時看一隻夜鷺停在綁繩上,沒在與我錯身時飛走,就停下來拍牠。牠表情冷靜沒有半點驚慌,我定著看了很久,直到發現另一條繩上扯著一隻飄在水面上的屍體才意會過來。
我想到小時候阿嬤從魚塭帶回一隻陷阱逮住的大鳥烹煮,拆解下牠的爪子,拉著一條筋跟我說大鳥足部的運動構造。我看著爪子隨她拉動肉筋的頻率張開、收合、張開、收合,再看看自己的手掌,張開、收合、張開、收合;是還沒上過自然課,但對皮肉下覆蓋住的筋骨有了點畫面,興味盎然。
阿嬤後來帶我去看那面架有快兩層樓高的網,立在漁塭岸邊。
鳥禽與魚類的生死場面小時候看得多,總以為這就是我長大後會選念三類組的原因,卻十分沒用地成為極其怕宰割畫面的人。大學生理心理學課堂上到一章,1992年科學家在靈長類及鳥類身上發現且提出了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的存在,從而推論其與人類得以發展出語言及共情(同理)能力之間的重要關係。
鏡像神經元的特別之處是,它在個體自己實際執行某一項行為,以及觀察到他人作出那項行為時,都同樣會被激發。也就是,當下是我痛得皺眉還是看別人痛得皺眉,單看其對應鏡像神經元的活動狀態,是無法分辨的。
心理學研究中,除了常見用猿猴、老鼠或貓狗進行認知實驗,行為心理學家史金納也愛用鴿子。著名的史金納箱(Skinner box)即經常是以飼料餵食制約鴿子以喙按鈕。此外已通過鏡中測試(mirror test)研究的動物,除了猿猴、海豚、虎鯨等哺乳類動物外,就是體型相較小了許多的鳩鴿和歐洲喜鵲。人類呢,則是要到18個月大之後才開始有意識知道鏡子裡的是自己。(如果在社群上看了夠多狗對鏡子裡的自己狂吠的影片就會知道,狗這部分是真的不太行)
以人的角度來看,鳥夠聰明,也體現於牠們能發展出近似於人類語言的聲音系統;鄭宜農在她〈人如何學會語言〉歌曲尾奏唸了吳明益《苦雨之地》同名篇章裡的一段:
鳥在飛行間鳴叫,為了社交而鳴叫,受了傷鳴叫,進行領域保護而鳴叫。一隻幼鳥孵化發出乞食聲開始,就不斷學習用不同的聲音表達自我——哪時候是愛情來了,哪時候是要離家了,哪時候是返家,哪時候是較勁,哪時候是絮絮對話。
而書裡接著反詰:即便多數研究指出鳥類鳴叫聲具有「方言」的特質且能後天學習,卻仍無人敢說此可以作為鳥類同人類擁有「文化」的證明。
養殖漁民是為了防止大鳥食塭仔裡的魚,才綁細繩設下陷阱的。
我停在那裡好久,直盯著綁繩上大鳥的眼睛看,像竊賊一樣左顧右盼,想偷眼前的生命。扯了扯細繩,試圖鬆開,但又怕魚塭的主人過來理論,還拿手機上網查了動保法是否有相關規範。我懂我想偷的不過是立基於個人因見著而難受的憐憫,大鳥欲食人養殖的魚而受困,而魚肉鮮美,不也是為上市場採買的我們而放流。
成長經驗不一樣就是不一樣。這是我把自己丟到台北生活幾年後才接受的道理。
當有人看著魚販將一尾鮮魚拍昏、刮鱗、剖肚、去內臟後切剁成乾淨的魚塊卻喊著殘忍時,我總會不解地歪著頭想:「但那不是你等等要吃的嗎?」五十嵐大介漫畫改編的電影《小森食光》裡一段對白就會很尖銳地跑到腦袋;城裡的人滿口仁義禮智,卻要人替他們殺生。就是連嫌惡高雄工業區景緻的話語,我都會苛刻地問,可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供應,我們不可能從任何產業中斷裂出乾淨的自己。然而說出「他們好髒,我好乾淨」這樣的話是多容易。
曾去大林蒲參與影像工作坊,2012年金甘蔗影展首次離開橋頭移至大林蒲舉辦,講師說有個參與影片競賽的男孩就在煉油廠工作,下了班,卻仍加入反石化工業與遷村的抗爭。我們如何能,意識到自己必然是身處於結構,卻仍努力地成為個人呢?
C傳了一張翻拍書的內容給我,是節錄美國神經科學家勒杜克斯說的:「一個人能不能有感覺,取決於他有沒有能力察覺他的自我,以及察覺自己與世界的關係。」W在他的Podcast節目裡則唸了一段義大利共產主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說過的話:「普通人能感受,但沒有辦法總是可以認識或理解。知識份子可以認識,但常常不能理解,尤其是常常他們不能感受。知識份子的錯誤在於,相信人們在沒有理解,甚至沒有感情,和沒有熱情的狀況下能夠去認識。」我拿這些話,其實也就只是想拐著彎罵不必持刀或進出工業區工作的知識份子。
最乾淨的事便是,所有不必實踐而只消論述。永遠站在結構之外論述。
收魚的時節,常有人會送來塭仔裡面混養的雜魚。有次收到一隻好大的土虱,不是平時看膩的虱目魚或吳郭魚,我好奇牠身上的滑溜和寬扁魚頭上的鬍鬚;阿嬤說這款魚很兇,就是要用刀背一直敲牠的頭,直到把牠敲昏。邊說,我就站在一旁看她舞動著胳膊,刀刀奮力直落魚首,五下、六下,牠才奄奄一息地任她宰割。其餘魚種,她也都能處理俐落;那年紀我讀游伯龍《智慧乾坤袋》漫畫講庖丁解牛的故事,動人處不光是庖丁那把刀能用十九年而未鈍,而還有那句:「刀鋒在牛的筋骨縫隙間來去,牛不覺痛苦,更不知牠已死去。」
阿嬤也養雞,雞仔囝是撿來的。劉家村的社區活動中心對面有個孵蛋場,還在運作的時候阿嬤會帶我去撿小雞。一台藍皮貨卡後面堆了滿山黃色、黑色的小雞,阿嬤說那是要被淘汰的雞,因為不健康,所以不要了。我抬頭仰望努力想探,掉下來的只有唧唧喳喳的聲音,一層壓著一層,上面的生命踩踏著下面的生命。伸手接她從裡頭挑出來的小雞,擺進紙箱裡,帶回家用破毛巾、報紙鋪底,開一盞檯燈讓牠們取暖。大了放養雞舍,母雞生蛋,公雞則在逢年過節時抓出來殺掉。
刀子劃過喉嚨,咕咕咕的聲音漸弱;不是最初從小貨車後斗掉下來的唧唧喳喳,而是一輛火車駛近之後又駛遠,載走靈而餘下肉身,成為食物。
大學在一堂播紀錄片的課上看了《美味代價》,才知道那成山的小雞接下來要不被碾碎、焚燒或讓土掩蓋。活著反而沒有價值的存在。佔用空間與資源的存在。而我蹲著、捏著她從雞魚體內挖出要扔掉的內髒,問:「這是什麼?」她就耐心地一一替我解答:
「膽,捏好,破去的話青色的汁流出來會苦。」
「雞胗,內底是猶未消化的物,愛含膜做伙剝落來。」
一邊翻看牠最後餐吃了什麼,來去都有蹤。
有隻小雞特別瘦弱,就撿出來獨自先豢在家裡。小雞亦有印痕,日夜就屁顛屁顛地對我跟前跟後,我以為取了名字是寵物,但最後大了還是混在其他雞群裡面宰掉。除此之外,我甚怕公雞。有次在園仔裡面被雞追,跑在苗圃間的廊道,剛噴灑過水的地極濕滑,我一急便摔跤,跌坐地上放聲大哭,最後被阿嬤拎著去給人用米杯收驚。
姊姊大我五歲,待她稍大之後就不再是我玩伴,我能獨自鎮日在苗圃裡玩耍,抓豆娘、蝌蚪和青蛙。我曾為了想擁有好不容易抓到的豆娘而掐斷牠翅膀,甚至將小青蛙帶到浴室裡洗澡時玩,卻不小心讓牠從排水孔沖進下水道,又或是被極燙的熱水燙死。我不確定自己是到多大年紀才意識到那樣「殘忍」,也或許由於我讀不懂豆娘與青蛙的表情和語言,好奇探索的本能先行,鏡像神經元置此無用——從而知曉人或許未必擁有同理與憐憫的本能。
人讀了什麼樣的童話,因而在自然之外的人文設下如何的道德準則,也形成了經驗之外的抽象的真實。
我印象裡第一個喜歡讀的童話是國際少年村版本的《格林童話》全集。裡頭不乏(或說根本充斥)〈森林中的三個小矮人〉之類,壞後母虐待自甘奉獻的善良繼女,最終卻反遭浸水桶推滾下山的故事;這樣不合邏輯地付出最終換得幸福餘生的寓言,好像或多或少變成某種浪漫至愚昧的成長隱喻。就算全世界的人鏡像神經元都癱瘓,命運還是會替你復仇。
再後來從家裡書架上翻來一本鄭清文的《天燈・母親》,代言苦痛的卻是土地公領著的一群鬼魂——對動物惡作劇最後卻遭毒蛇咬死的小孩阿灶、被大姑婆逼著吊死的三嬸婆,還有其他沒手沒腳或拉長著舌的冤魂。彼時才意會到殘酷不止在於列維納斯「不可殺人」的最基礎道德律令,因為書載的台灣早期農村生活是就算死了還有的生死觀,以及阿旺多出來的第十一隻指頭彷彿所羅門王的指環,能與牛、蛇、青蛙甚至稻草人對話、傾聽他們心聲。
作家陳玉玲導讀此書,引用榮格心理學派卡蘿・皮爾森的論述,寫小孩主角阿旺代表著「聖嬰」原型,「超越了人鬼神,人與動物,生物與無生物之間的界線」,緣此大愛化解衝突,並拯救了因產他而死的母親鬼魂。在鄭清文的童話裡,天燈是能載冤死鬼抵天聽的最後救贖。阿旺從樹上撿來破掉的天燈、修補完善,土地公一面替他們管理其他想搶乘的冤魂秩序,一面交待一只天燈除能載他母親外,還可多帶上兩隻動物;「阿旺和阿秀幫母親選了兩種最可憐的小動物。一是蜻蜓,一是青蛙。」
讀到這段,內心匡噹。我總感覺那些動物的靈魂一輩子都跟著我了,但亦不算是壞事。
我不大為年幼的自己所為感到負罪,只是長大後偶然在城裡看見在路中間徐行的蝸牛,忍不住會停下將牠們捏起來擺到路邊樹叢。如此徒勞的行為,試圖要贖的記憶還有,爸和阿嬤在雨後將非洲大蝸牛拾起再用力丟擲地面摔破的畫面。我見過稻農也是這樣操作,於是你會看見臨稻田溝渠邊的柏油路上,一攤一攤地曝曬著碎裂的福壽螺屍體。
我用智識去理解,不可讓強勢外來種侵略本土生物,牠們亦會十分放肆地啃食無論花苗或稻穀作物。原來我恐怕沒有自信說那不是罪。
前陣子聊到隔壁巷燒陶的舊識,爸媽說他原想和我們租塊小地做磚窯,但後來卻沒成,「伊著講伊去問神明,神明交代講莫殺生啦。」久沒整理,我們那片苗圃已經變成人難跨步進去的原始樹林,數不清的鳥、蛇、蛙與昆蟲已形成牠們自己的生態系,「這些相思樹,為了造一條新路,有一半以上要砍掉,那些白鷺鷥將怎麼辦呢?還有那些墳墓?」阿旺在走去給母親送天燈時,面對庄子即將的開發也冒出許多疑問。
要是沒有人告訴自己,人會有一刻意識到自己其實殘酷嗎?人是不是天生其實就殘酷呢?我曾經在讀到鏡像神經元時,以為自己找到人類或許本善且能利他的證明——既然它能使我們感同他人疼痛,那人應當不忍彼此傷害才是?但又為何經常,我們需要感到疼痛的他者提醒,才知曉自己無意間作出傷害呢。
語言與共情,還竟被心理學家認為高度相關於同一類型的神經元上。
倘若鳥也有童話,牠們會如何傳唱吟詠,當一邊的翅膀纏住,另一頭的夥伴已在氣力用盡之時溺斃水裡;萬一我有把刀可以把繩子割斷呢?於是那夜半的雨我聽得難受。
對這類事情的判斷,我心總是沒有著落,要人堅定推我一把,才能勉勉強強地降在一處稍息。常懊惱自己站不定立場,做或不做心安理得的事,很難受,更不想忘記,對著大鳥拍了張照片。隨後看幾隻狗開心在堤上跑跳,便又興奮地忘了,直到深夜雷響雨落。當我把自己看作行動者,就會變得非常不敢於批判事情,這個狀態多年來始終沒有改變。然而憐憫有時候卻很弔詭,更無法確知那一亮一滅的神經元是為什麼樣的真實代言;有了這層理解,純粹的初心與動機也變得不再是那麼值得讚揚的事情。
我們需要知曉,不斷質問,而不是期盼一勞永逸的結論。縱使如此會令我感到脆弱。
〈倘若鳥也有童話〉的書與歌單:
《苦雨之地》吳明益,新經典文化
《智慧乾坤袋》游伯龍,洪建全基金會
《天燈・母親》鄭清文,玉山社
《格林童話全集》格林兄弟,國際少年村
〈人如何學會語言〉鄭宜農,火氣音樂
〈全心全意的愛你〉吳志寧,風和日麗唱片行
related articles/ all about Liu Village
±06 舊聞❞ 留家村:愛河岸邊沒有留言
去看巨轟演出,聽魏talking聽到差點掉眼淚。2013年畢業後我就上台北念碩,與高雄的道別有點狼狽,無論和系上朋友、樂圍或家裡,都有些微妙而掐不清的思緒。即便我經常懷念,卻仍感覺上台北有些逃的意味。不過都是十多年的事了。2022年拿了Y的票去大港,睽違那麼久與猴子碰到面,是真正大學畢業後再也沒見的朋友,回家後和猴子聊天想起許多大學時愛河岸邊沒有留言的事,遂寫成了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