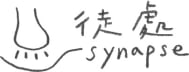±09 舊聞❞ 留家村:戶聲
過去我總在頂加雅房眺望整座城市時才想起自己身在廣袤宇宙,那些貼得很近的瑣碎變成了背景,生命反而在一片虛無中成為主體。而人之將死則成了時間向度上的變焦鏡,調調轉轉,曾經我們都還在的日子,過去的愛會成為未來孩子們的鬼。
——20211117
2020年的最後一日,在朋友家看晚會直播也算是跨過了這動盪、糟糕至極的一年。凌晨接近一點,家裡群組傳來媽的訊息,說稍早(也就是「去年」)外公過世了。那瞬間感覺甚是奇異。
從跨年夜算起,我原本就排了整整11天的特休假待在高雄,突然全變成了喪假。告別式上舅舅說:「謝謝爸,讓一切病痛都留在去年。」那一刻的感覺是,爸媽都真正成為沒有爸媽的小孩了。
後事處理得很快,小時候說「轉去高雄」的前鎮外公外婆家也決定轉賣給隔壁鄰居,媽知道我很喜歡外婆作為嫁妝的那只老櫥櫃,便問了舅們是否能留給我。前幾天,趁著工程開始前我們從湖內開貨車去載,外公住安養院後已經許久沒去,我想上樓探探但時間緊;掉在樓梯口的光是從二樓面國中的那間房來的,我以為還有電視機的聲音也和在漂浮空氣中的毛絮裡,可回過神後什麼也沒有。
載回櫥櫃的隔日我就上台北工作,採訪因著國慶後的颱風改期,待了一週多。週末同以前還住台北時的尋常,散步到建國花市晃晃,大概受到10月19日後放寬的二級警戒振奮,人潮更要晴朗的日子多。我是太久沒在這麼多人類的地方走動,想辨認這種不過暌違半年的陌生——除了固定不變的公寓大樓填滿天際線外,好像是聲音嗎?聲音的景深也隨天際線變得好淺好淺,只剩方圓五公尺內的動靜,之外的再多都像不存在一樣。
有陣子到山裡,常想起以前知覺心理學課堂上一個最開始就被拋出來的哲學問題:
假如一棵樹在森林裡倒下而沒有人在附近聽見,它有沒有發出聲音?
If a tree falls in a forest and no one is around to hear it, does it make a sound?
這問題被我帶回城裡繼續思考,「要是不被聽到就等同於沒有發出聲音,那在這個城市裡靜默無聲的人事物也是真的太多了。」又像詩人T. S. 艾略特《四首四重奏》〈小吉丁〉裡寫大河的源頭以及蘋果樹林裡,躲藏著瀑布飛湍與孩子嬉鬧聲,卻全都因為不被聽見而不存在。
我很喜歡當時在台北的兩個住處,一是在師大夜市小巷裡,另一則在同安街尾,都是老公寓六樓的頂樓加蓋。頂加之美妙便是明明位於都心卻能遺世獨立,像是相機鏡頭光圈開到最大,視覺和聽覺上的景深在不斷變換對焦時展現空間感。週末上下樓間,還能聽見門縫一點一點漏出鋼琴和小提琴練習的聲音。
小孩整個月都彈同一首,家教老師談不上耐性,這種看不見的存在經常帶我回南方。
劉家村裡的古厝與阿姆家貼得很緊,但又不是真的貼在一起。兩戶之間不過半米的防火巷各自都有開窗,阿嬤說小時候我老愛貼著窗對隔壁「保仔!保仔!」地喊阿叔的小名,電視機從《小叮噹》開始播到民視台語晚間新聞,晚餐後切好水果就已八點檔。舊家前門亭仔腳面對著另個阿姆家開在廚房的後門,傍晚抽油煙機啟動就飄來陣陣煎魚的油香。後來就靜下來了。焦段能對到的景深去到百尺之外的魚塭,風車打水,偶爾一兩台車忽地行駛而過。
大湖這邊的家能聽得更遠,住處不算聚落,一條路上才四戶,有時候清晨露水重,真的靜下來是連一公里外火車駛經的聲音都聽得到。不過也因此罵小孩或夫妻爭執什麼的,也都聽得清楚內容,更不用要猜是來自哪戶人家,難免隔日打照面要思忖著該不該裝作不知道。
前鎮外公家是透天厝,有個房間開在長長通往三樓的樓梯途中,小半樓很有《小叮噹》漫畫場景的感覺。小時候跟著媽回娘家,開車回程前她都會上樓午休小睡片刻,我有時也就仰躺在她身旁睜著眼對天花板發呆。陽台傳來街上有人對話,或房門這側樓梯底下外公看電視的聲音。有次她回想起她的童年,曾在深夜聽到神明著木屐在樓梯間走路的聲音,叩叩叩叩地穿透木隔間,走上樓,再來,就平空消失了。
想起電影《星際效應》裡的「鬼」其實是父親,自未來折疊起時空、穿過了蟲洞,為女兒帶來預示。當中有句台詞:「父母生而在世,就是為了在未來可以成為孩子們的鬼。」
我從小是在水平的景深中成長的,日光、聲響、我的步伐,除星體東升西落,其他則跑四面八方,但前鎮這邊則無論光或聲音都是垂直於空間流動。到城裡生活的這幾年,找不太到景深,事物總是不太客氣地直接撲到身上,人、聲音、氣味,可見的不可見的,空間縮得很小,就連工作任務都要我把一日切割成以半小時為單位的時間軸填塞進去。過日子也像是在捷運站被人推擠勉強著前進,視野的光圈如同連日陰雨,孔洞微縮,但也沒多少時間能夠等待曝光,遂成像得很暗。或許是這種暗,讓城市需要更多色彩或新的物件填進來,在有限的景深裡安排自己少數可控的畫面。
咖啡廳播的爵士樂要大到蓋過對談、IKEA書桌純白得能襯出好看的攝影書、辦公桌上每週一束鮮花則盛開到能遮掩職場上的無奈。下班後聚會聊些什麼呢?這些日子突然離得遠,在城裡挑了家咖啡店偷聽鄰桌的人聊職場聊創業,細細想比對只有五公尺內景深的地方,曾經是如何運作生活。
這幾天的風雨在城裡,相較於建築物和騎樓,街道上的雨不是主體,而是過渡——傘是用在空間與空間之間的過渡。
可是這在地方卻不是這樣的。
整片雨才是主體,遮蔽處才是過渡;具有空間感的寂靜是主體,對話才是過渡;天空是主體,建物才是過渡。像這樣的造樣造句能夠無限延伸下去。漁村寬闊的視野經常被我看成生命之隱喻,「主體」和「過渡」之間的定焦轉換,很像是工作或者整個生命,究竟何以為主體何以為背景——不忘作為一個個人的決定。
阿嬤剛過世時,有天爸聽到廚房砧板掉落的聲音,他說:「囥佇咧彼爿無可能是家己落落來的。」媽補充:「恁老爸就感覺是阿嬤轉來矣。」過去我總在頂加雅房眺望整座城市時才想起自己身在廣袤宇宙,那些貼得很近的瑣碎變成了背景,生命反而在一片虛無中成為主體。而人之將死則成了時間向度上的變焦鏡,調調轉轉,曾經我們都還在的日子,過去的愛會成為未來孩子們的鬼。
你知道宇宙每分每秒都在膨脹嗎?星體之間的距離將逐漸遙遠,空間與時間的無限,讓此在顯得好小。但在生活裡頭,我總得靠那些緊鄰的戶聲與逝去的人,才得以推導出時間與空間的概念。
〈戶聲〉的歌與書單:
《一平方英寸的寂靜》戈登.漢普頓、約翰.葛洛斯曼,臉譜出版
《幽靈、死亡、夢境:榮格取向的鬼文本分析》安妮拉.亞菲,心靈工坊
〈A Dialogue Between Me & My Ghost〉何欣穗,博樂伯樂
related articles/ all about Liu Village
±06 舊聞❞ 留家村:愛河岸邊沒有留言
去看巨轟演出,聽魏talking聽到差點掉眼淚。2013年畢業後我就上台北念碩,與高雄的道別有點狼狽,無論和系上朋友、樂圍或家裡,都有些微妙而掐不清的思緒。即便我經常懷念,卻仍感覺上台北有些逃的意味。不過都是十多年的事了。2022年拿了Y的票去大港,睽違那麼久與猴子碰到面,是真正大學畢業後再也沒見的朋友,回家後和猴子聊天想起許多大學時愛河岸邊沒有留言的事,遂寫成了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