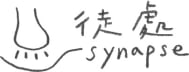±10 舊聞❞ 留家村:藍鯨
颱風是怎麼走的?通常是倏地一陣平靜。但你要判斷,這是因為颱風的眼睛走經才暫時解除空襲警報,抑或它真正遠離。在那之前只得任由香蕉苗被吹斜、滿樹的龍眼被打落。我們按壓住紙板,而不能離開一步。
——20220811
一頭成年的藍鯨能有24公尺那麼長。小時候讀到這個資料,有點難想像這個數目字的概念,大人說,走一步當一公尺,走24步就是藍鯨的大小。那比房子還大!小腦袋裡浮現畫面,一頭比房還大的藍鯨躺臥在屋子旁邊,恰好房子洗石子的外牆和瓦都是灰藍色的,宛如又另一隻藍鯨休憩在那。
去年盛夏南方雨出奇地多,我房間書桌正上方的瓦掉了幾片,只要雨勢稍大就會漏水滴答。我忍耐度一向高,台北還住師大頂樓加蓋時曾一次颱風夜,天花板一塊輕鋼架矽酸鈣板吸飽了滲漏的雨水,最後碎成柔軟的落石坍垹在床尾,我也就拍張照上傳社群笑笑。但漏水在書桌可就不好玩了。接案工作者多依賴那張桌子,一落一落的雜誌和書,還有筆電都是生財工具;那陣子夜裡不敢睡沉,就等雨聲隨時把我拉出眠積澱成的潟湖,在即將做洪之際,一個箭步就衝去把水桶對位到水滴下來的地方承接。
許久未想起藍鯨,那時又感覺自己就是被吞進鯨魚肚子裡的皮諾丘,潮濕的日子燃起鼠尾草和秘魯聖木消霉味,喚醒鯨魚打了一個噴嚏。
我的這頭藍鯨是磚造的。
大湖這塊地,據說是早逝的阿公年輕時拼下,後來爸將大部分的地做花卉種苗場,剩下的才蓋起我們現在住的房子。僅一樓的平房,他用薄木板先手工黏過結構模型,是有東西向雙斜屋頂和羅馬柱欄杆圍籬前廊的小屋,屋的四面都有窗。在我僅有的印象裡,這房子還在施做工程時我們天天從姓劉仔那頭過來監工,蓋屋的工人還撿來一窩幼犬,集在黑色塑膠籮筐裡說要分回去養。留下幾張照片,是媽摟著我和姊坐在一落落被姊妹倆砌成人面獅身像的紅磚前合影。那放任我們玩的空間最後蓋成了有木板通鋪和木拉門衣櫃的房,是阿嬤一直以來睡的房間;很小時候我還跟著她睡,好幾次她說她見我夢遊走到床緣褲子脫了就要坐下尿尿,她便一把將我抓去廁所解除警報。
除此之外的幾間房我也都睡過。長大後才知道換房睡不是一般家庭常態,但爸媽非常熱衷於更動家具擺設之類軟裝格局,每隔幾年都會輪換空間做書房和臥寢。這次搬回來,我便預先選了那間有通鋪的房成自己空間。
雨季過後接續是颱風揚起風浪。
小時候最喜歡颱風天阿嬤才會弄的鍋煮統一肉燥麵加蛋,但又最討厭她在颱風天時說要出門。颱風天明明最不該出門,老人家卻總放不下心那一池池魚溫,若看電視新聞台播報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她就要趕在風雨來之前騎腳踏車去海埔的寮仔把風車、飼料桶的電源都巡過。當電視天線被吹落,我們就改聽收音機,很小心翼翼地微幅調動FM調頻轉扭、延長天線在空中畫圓找訊號,要讓雜音減至比風雨吹響門窗的聲還低。
自個兒獨建的平房,環繞的浪要把我包覆,但藍鯨知曉如何避浪,只是牠有年負傷。
那陣子經常酒醉的男人幾乎把我家每扇窗都打破,小石子是從要入我家前庭的上坡地撿的,只要天黑我就害怕,隨時預備著匡噹聲隨夜色投進屋裡,即便阿嬤已經把每間房的窗簾都很好地拉上。玻璃窗破了倒還好,至少還有一層白鐵窗能確保安全,然而風雨是無形的,輕易就能竄入。她偷著隙縫,在陣風與陣風間拾來一塊紙版要我和她一起壓住破窗的洞口,她說要不如此,風會把整片屋頂的掀起。我當時腦袋浮現的畫面很卡通,但其實早就嚇壞。
颱風是怎麼走的?通常是倏地一陣平靜。但你要判斷,這是因為颱風的眼睛走經才暫時解除空襲警報,抑或它真正遠離。在那之前只得任由香蕉苗被吹斜、滿樹的龍眼被打落。我們按壓住紙板,而不能離開一步。
我想逃跑
——但我害怕逃跑
倘若離開了屋瓦
我會餓,衣服會皺
雨不會離開
詩會死
我不能逃跑
因為我害怕屋瓦
——《我害怕屋瓦》,曹馭博
從小我就容易有被追殺的夢,在我筆記過的夢境裡,有十幾二十次都關於逃亡,而且每次都能搬演出不同情境——在火車鐵軌上、半掩的門扉、街邊停車場、大樓樓梯間、像是塞納河的河畔、有飛機的大草坪⋯⋯總是美麗的場景與離奇的劇情,並且每次追我的人都不認識,有男有女,通常則不具有可辨識的臉孔特徵;那個人物形象,往往只是一種「感覺」。最好笑的是有次夢到追我的人是公司打掃阿姨,結果隔天進辦公室,一早阿姨拖著吸塵器靠近要吸地,我嚇了超大一跳只差沒叫出聲。
壓力大的時候尤其容易做被追殺的夢,但自去年開始,我已經好久好久都沒夢過逃亡了。翻了翻keep上關於夢的筆記,最後幾次逃的夢分別是在前年五月初和八月底;五月那次,是個在鄉下小鎮被跟蹤的場景,而想起國中有次從補習班下課,獨自在小鎮街邊等爸媽到晚上快十點,卻遇到一個腦部有開刀痕跡的少年不斷尾隨、逼近。我一直是個不擅長求救的孩子,更討厭被發現自己其實有需求,會走到離補習班有點遠的地方其實便是怕被老師發現家長還沒來接;而即便這樣的處境,我仍寧可一個人躲進別人家後門車庫,也不願去超商或敲門找人幫忙,並也是知曉對方並無惡意,只是腦部損傷而無法控制自己的行徑。有些憐憫,卻還是在被接上車後生氣地哭了一陣。而八月的那次則不再是獨自奔跑了,有個男生開車要我們上車,他說:「逃難的時候也想要有人陪伴啊。」
那之後,我竟再也沒做逃亡的夢。這件事的奇異在於,前年五月我恰巧多次恐慌發作,每次感覺都像感官被開了門,然後記在身體裡的可怕被釋放出來。很累、很麻木,腦袋被一種波頻包裹著,外在世界暫時變成另一個陌生的維度。而現在回頭看,那更像是埋藏地底許久的深層餘震,逃亡的夢是潛意識企圖攀越上表意識的窗,叩叩叩,她以最溫柔的力道輕敲,只得等我足夠疲憊的時候才被放行。
她持燭火點亮海馬迴的一角,然而到白日我又捻熄了燈。


國中開始常為了趕考試進度徹夜讀書,我讓桌子靠窗,得臨馬路那面對窗而坐。我睡中間和室,與窗相臨還有一扇金屬製的後門,推開是花圃,接攘小時候摔過數次的小水溝。我喜歡雨夜,就像袁瓊瓊在她一篇極短篇裡寫,「有時下了雨,黑夜像給雨洗褪了色,大片大片的脫落著,慢慢的彷彿不那麼黑,透明了起來。」第一次讀到時,正好是暑假來臨前的梅雨季,覺得原來這就是作家的厲害之處,能把我無法形容的知覺感官如此精確地用文字轉譯。更小時候,雨夜也令我安心,因若大雨滂沱,那男人自然也不會前來造訪。
鄉下地方睡前屋門不鎖曾是常態,即便當時透天厝騎樓多會加做鐵捲門,但也鮮少見鄰居會將其拉下。第一次他來,家裡只有我、小六的姊姊和阿嬤。大概是由苗圃那拾來一把工具箱裡的鐵鎚,碰碰碰地把木門敲破,接著一隻手從洞口伸進來,反手將兩道門鎖打開。阿嬤見狀對我們疾呼一聲:「對後壁門緊走!」就有雙小手拉著我從後門赤腳跑到鄰居家騎樓,我們屏氣,身軀直挺地,背緊貼著側邊降下的捲門,不敢發出一個聲音。直至阿嬤沿街叫我們的名字,兩個小孩才從捲門後探出來,跟著她走回家裡去。
他連來了幾次,不堪其擾地,我們後來只要入夜就回舊家睡,且夜晚僅能留客廳神明桌的紅蠋燈而不能開日光燈;黑暗由裡而外,沒有雨能將那段時光洗得透明,猶如藍鯨也跟著我們閉氣潛伏於深海。晚餐是先在藍鯨肚子裡烹好,一老兩小先吃飽、洗漱過了,再用鐵製圓便當盒盛一份留給從台南下班回家的媽媽。她會輕敲家門,說:「我,娟仔。」阿嬤才會將多道門鎖由內一一轉開。
而那設計建造藍鯨的人暫且先出海至鄰邦去了,獨留我們在這抵擋著侵擾。
如果這處居所是頭藍鯨,那當時在台南母女三人第一個短暫棲身的小套房就像沙丁魚群。年紀太小其實記不太清楚,只依稀印象那套房是輕薄木頭隔間搭起的家,入門即面一張雙人床,床尾離電視櫃僅有一米空間轉圜,有扇對外窗,樓下則是有整排遊樂器的電動間。一切都孱弱得不足以撐構起家的主體,卻是群飛候鳥呈象於完形的共同命運律。也不知道當時媽打哪弄來一個鐵製鬆餅機,買了一包超市的便宜預拌粉,十分克難地和我們攀在窗台鐵欄杆上烤鬆餅。小套房在一個午後膨脹出甜香,在我尚陌生的城中撐出了空間。
兜來轉去,大概一年後又回來藍鯨,某年爸批來好幾綑的細竹子,在苗圃的工作間要築起一幢竹屋。他剪了一束一束的細鐵絲,交給我一把鉗子,讓我幫他將竹子固定上去。從房子到竹屋這邊夾著一片植滿數十種香草植物的花圃,光薄荷就有十多種,像是摸貓那樣輕輕撫過,就能蹭得滿手清香。那段時間都要把煮好的晚餐端過去吃,飯後點起蠟燭熱玻璃壺裡的水,塞入新鮮的香草或果粒煮成茶,我打開音響聽廣播寫評量和學校週記。小學六年級,覺得從家門經花圃到竹屋那端是很遙遠的距離,總要用跑的經過那條,他或許亦曾為拾鐵鎚而走過的無光的步道。
長大後每每站在已經荒煙澷草一片的小徑前,望著另外一端久未整理的竹屋,都會想,不遠吶,其實兩端的距離並不遠,小時候怎麼會這麼害怕這條小徑呢?沒有想過長大後身體對於距離的體感早已改變。而如今任憑風雨多大,我也都不再向屋瓦禱告。詩人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具受屋瓦保護的裸命。」
無要緊 無要緊/雲明仔載會開/雲明仔載會開
——〈做風颱〉
〈藍鯨〉的歌與書單:
《我害怕屋瓦》曹馭博,啟明出版
《袁瓊瓊極短篇》袁瓊瓊,爾雅出版
〈做風颱〉鄭宜農
〈一枝草〉百合花
related articles/ all about Liu Village
±06 舊聞❞ 留家村:愛河岸邊沒有留言
去看巨轟演出,聽魏talking聽到差點掉眼淚。2013年畢業後我就上台北念碩,與高雄的道別有點狼狽,無論和系上朋友、樂圍或家裡,都有些微妙而掐不清的思緒。即便我經常懷念,卻仍感覺上台北有些逃的意味。不過都是十多年的事了。2022年拿了Y的票去大港,睽違那麼久與猴子碰到面,是真正大學畢業後再也沒見的朋友,回家後和猴子聊天想起許多大學時愛河岸邊沒有留言的事,遂寫成了這篇。